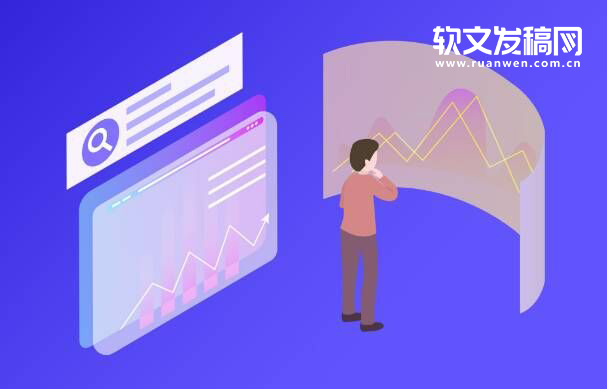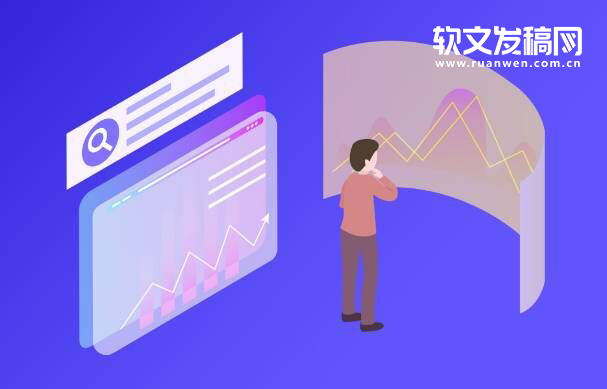前言
工业化社会之后,城市作战越来越变成了战争的主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有40%的战争发生在城市和大的居民区;二战后美海军进行的250多次对外军事干涉中,有90%涉及到了城市。城市的安危得失将成为战争胜败的重要标志。未来的军事行动或许将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地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战争发生的主要空间。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本文无意也不会讨论复杂的地缘政治,而是聚焦于微观的战术行动对城市空间的颠覆以及再组织。
通过解读一篇对以色列总参谋长科哈维中将的采访稿整理出的论文,详细论述战术指挥官如何将一些抽象的空间理论运用到了具体的城市战术行动中。以供读者参考。
城市作战的空间维度
在古代,战争一般发生在野外。首先这是因为古代的城市化率低,其次广袤的空间有利于大规模军队的集结和阵型的展开。即使古代有着攻城战,但只要突破城池进入巷战阶段,基本标志着战争进入尾声。
▲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被炸毁后,奥斯曼苏丹轻易的攻入了城池
但与之相反的是,现代的城市巷战不再是战役的尾声反而是战争的开始。比如二战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役。
1942年8月19日,德军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9月10日,德军的先头部队进入斯大林格勒市区,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人类史上最残酷的巷战展开了:城市中的每个地点都变成了战场,德军往前推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直到整个战役结束的时候,德军都未能控制整个城市。
除了苏联人民英雄般的意志以外,城市空间本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野外的遭遇战更多的只是在二维平面展开(不考虑空投部队),那么城市作战无疑是三维和非线性的,高大的建筑物和四通八达的地下工程设施让战场环境异常复杂,狭窄的街巷分割了大兵团的协同指挥,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的机动小队。
总而言之,当代城市作战是在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建筑中,通过对空间的破坏、构建、重组和颠覆来进行的。
如何根据相关的城市空间来调整战斗部署,以及如何根据需要调整相关的城市空间,这个相互反馈的过程,是城市作战中一个永远值得讨论的问题。
而在下文中提到的科哈维中将的城市作战理论则是通过一系列微观的战术行动去改变“墙”这一建筑元素,从而重新去组织城市之中的空间关系。
城市巷战中的墙体
在阐述之前,我们需要对“墙”这一概念做一个简短的谱系学的考察。
“墙”是什么?在物理上它是用砖石土其他建筑材料筑成的屏障或外围。在空间上,它标志的是一种界定,在古代社会,城市周围的墙,界定了城邦主权的区域;私人住房之间的墙,担保了私密性。
而在现代,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了,“墙”作为一种私人的“微观主权”发挥着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非法侵入住宅罪就能知道了。
也就是说,“墙”发挥着一种禁令的作用。
好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以色列国防军的 “行动理论研究所”的所长自称他受到屈米以及德勒兹影响很大,尤其是曼哈顿手稿,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屈米的 ‘分裂’ 理论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思考范式突破了单一的视角和中心化的思维......
屈米将行为、空间以及其(空间的)表现形式概念化,(屈米的)《曼哈顿手稿》给了我们一种制定行动时不用再去地图上面简单划线的工具,他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符号。”
▲屈米解构主义园林的代表——拉维莱特公园
为了读者的理解,笔者有必要解释屈米的“分裂”理论以及《曼哈顿手稿》是什么:简而言之,“分裂”打破建筑功能的使用与建筑空间和形式之间的常规联系。“分裂” 的核心内容就是 “事件一空间 ” 。屈米认为,空间中的事件应该是多样、 功能不明确的——它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结构中。
▲摩天大楼的每一层都彰显着功能和形式的分裂
“分裂”理论的运用我们可以在屈米的《曼哈顿手稿》中可以看到。在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筑摆脱了传统的线性阐释结构,而时刻于一种动态的事件-行为-空间的三元叠加中。(在屈米这个三元组中,事件是上文中将军提到的space,而空间则是将军提到的 its representation)
也就是说,屈米把人的行为加入到建筑之中,将事件、运动和体验看作是一种叙事性的线索。空间摆脱了通常的预期,按照一系列戏剧化的能够提示一种新的空间结构来进行表演。
▲手稿关注的始终是建筑发生了什么,而非故事发生了什么。
科哈维中将则通过重新定义”墙“,去重新组织了整个城市的空间。
在传统的空间定义中,墙的空间功能使用是禁令,但是在微观战术行动的改变下,“墙”由禁令空间变成了可以自由穿梭的交通空间。“墙”固有的形式与功能在屈米的意义上发生了“分裂”,对此,他是这样描述这种战术方法的:
“我们不会像传统的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师那样把小巷解释为交通空间。
我们把小巷解释为禁止走过的地方、把门解释为禁止通过的地方、把窗户解释为禁止看的地方......这是因为敌人是以传统的方式来解读空间的,而我不会去遵守他们的指令从而落入他们的陷阱。
我们使穿墙这种微观战术变成了一种通行的方法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整个空间。”
▲城市路网标记的是“禁止通行”
破墙开路
纳布卢斯(一座巴勒斯坦中部城市)的战术行动被认为是科哈维中将“空间理论”的一次有效实践。
由图可以看出该城市中心地带建筑密集,路网四通八达,对于防守方的作战十分有利,通过在小巷上放置路障以及在建筑物高层设置狙击点,几乎每个街巷都可以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覆盖。
▲纳布卢斯整体的路网系统
▲纳布卢斯市中心的路网系统
而事实上,游击队员也用油桶、战壕和成堆的垃圾和瓦砾来阻挡通往老城和巴拉塔的所有入口。街道和小巷沿途布满了简易爆炸物和油箱。甚至建筑物的入口处也有杀伤装置,整个城市可谓是武装到牙齿。
以笔者截取的下图为例,如果仅仅从A点移动到B点,就至少需要突破四处火力交叉点以及三处路障。
▲红圈为火力覆盖点,三角形为路障
但指挥官并没有选择沿着城市中现有的街道网络的进行线性的推进,而是使用了破墙武器(包括锤子和特制的穿墙弹)。从而让小队通过建筑中的“墙”来进行移动。
那么我们同样以上面的路径分析图为例子,通过这种破墙战术,我们可以看到,小队的线性路径被完全改写为非线性的侧面袭击。
这种“不走街道,不走正门”的战法,其最基本的前进方式是在建筑内打洞破墙,通过穿墙逐步推进;尽量不与街道平行推进,而是走斜线或不规则路线;尽量避免沿街运动或直接拐弯从直巷进入横巷。
当受地形限制必须从街道运动时,也要采用简易盾牌构成临时掩体;利用较高建筑物对街道和路口进行观察和扫荡。
在纳布卢斯老城区战斗中,士兵避开埋伏着狙击手和爆炸物的街道,穿墙而过,在游击队员的侧面、后面甚至上面突然出现,从而制造的致命打击。这种非线性的运动原则,完全避免了游击队员预设的地雷和伏击的杀伤。
▲红圈为火力覆盖点,三角形为路障
而在更微观的单体建筑里面,以军同样舍弃了传统的交通空间——楼梯。因为在传统建筑的攻防战中,这同样是被重点把守的空间,得益于先进的爆破技术,以军得以通过升降绳在天花板中炸开一个个口子而进行快速的穿梭绕后。(甚至说通过爆破就可以让游击队员坠落以造成杀伤,而爆破产生的大量烟尘和巨大声响正好得以让以军获得掩护并且震慑游击队员。)
虽然爆破墙壁这种战法很早就有实践,但是一般都用于单次的行动之中,而这次以军却有意于将其作为城市巷战的常规化模板进行使用。
据事后统计,纳布卢斯老城中心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被强行穿过,在墙壁、地板或天花板上都被凿开了多个口子。战后一位士兵这样描述道: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建筑物,完全是在住宅之间前进......我们所有的人——整个旅——都在巴勒斯坦人的住宅中,没有人在街上......,在整个战斗中,我们几乎没有冒险出去......”
在这次战术行动中,作为禁令空间来使用的“墙”在二维和三维空间均遭到颠覆性的突破。而在此之前,游击队员认为,作为禁令空间的“墙”,可以安全地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可当以色列的军队穿过一座座被炸毁的“墙”时,这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震撼和威慑。毫无疑问在这里,禁令空间与自由空间被完全交换了,以往可以自由行走的交通空间被凝滞,而禁令空间则被不断突破。
“墙”的传统功能定义由于人的行为运动,被彻底改变了。运动(或者说行为)被置入到了整个的空间构成中,而形式与功能的旧有关系被脱钩并且不断产生出全新的、动态的组合方式,由于“墙”要素的不断变化,整个建筑环境以及城市空间组织自然也产生了全新的路径图解。而以色列军方认为这种战法,无疑是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重新组织从而获得胜利。
▲城市中道路与建筑的关系被颠倒(红色表示禁止通行的空间)
法国大革命中的街垒
这种通过行为去改变空间要素本身定义从而反作用于空间的策略,其实并非是以色列军队或者屈米首创。
我们可以沿着历史追溯到18世纪的巴黎,这个城市可能是世界上经历各种革命运动最多的大型城市,从攻占巴士底狱到法国大革命中一系列的街垒战争,以及后续的巴黎公社运动和五月风暴。城市巷战的基因或许在无意识中早已刻入巴黎市民的骨髓中。
▲攻占巴士底狱
屈米曾直言,他的一些理论其实也是受到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在屈米看来, 在巴黎街道(形式)上筑起街垒(功能), 这一“事件 ”打破了功能与形式的稳定关系。屈米将其称为“交互设计”。这种事件与空间之间不稳定的联合具有颠覆性的能力, 因为它既挑战了功能也挑战了空间和形式。
如果说上述以色列军队的重点是如何将由“墙”划定的禁令空间重新阐释,那么巴黎的街垒则是完全相反。巴黎的道路自腓力二世时起就铺设石块作为一个自由行动的空间,但一直以来,这些道路上的石块都为街垒的修建提供了重要的资源。
在1650年,巴黎出现了一种服务普通民众的“公共马车”,这种交通方式发展迅速,至1850年时已拥有5000辆,而将其推倒后就地取材填充道路上的石块,便成了修建街垒的重要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行为对其要素的改变——运动的元素(铺路石和马车)变成了静止的元素(街垒)。
▲1848年巴黎街垒的密度
而巴黎人民恰恰是通过这些街垒,完成了对整个巴黎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通过街垒来分割巴黎的交通组织,每一个街巷,都成为了一座战斗堡垒。而1830年的七月革命无疑是这种街垒战的高峰——在没有统一指挥的前提下,这一天巴黎街头的街垒数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4000座!也就是说平均每200个巴黎人建起了一座街垒,规模庞大的街垒网络阻碍了王室军队的调动,使王室军队难以发挥数量和火炮等重型装备上的优势。
结语
笔者对军事的研究并不深入,如有疏漏或错误请各位谅解指正。此篇文章提供的只是一个从外部出发来观察空间的视角(事实上,屈米不就是从建筑学的边界之外来发展他的建筑本体论问题的吗?)总之,笔者希望此文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启发。
最后,祝世界和平,早日摆脱战争。
参考文献:
[1] Weizman E . Walking through walls: Soldiers as architects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J]. Radical Philosophy, 2006(136):8-22.
[2]荆文翰. 城市的抵抗——浅析19世纪革命浪潮中的巴黎街垒[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3(3):6.